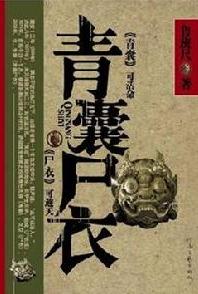第五章二月二十八日 (1)(7 / 23)
地至无可挽回的地步,领悟了以上这一点后,对他的打击颇大。他从没想到瑞浦的举动会是如此坚决严峻;而他自己的一切作为,都是建立在一连串的错误假设上。事实上,即使他对情势的分析正确无误,也挽回不了这名客户,不过安德森对自己的状况所受到的心理冲击,与此论点是毫不相干的。这么一个明显的错误,算是无法见怪的情况失控;至此整个情况全弄拧的安德森,离开铺着深紫红色地毯的房间时,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转变影响了他的思绪,并且自然而然地扩及他的行为。在欧洲文明国家中,有两种重要的社会阶级,其一是做事的人,其二是把事做完的人。安德森走进铺着深紫红色地毯的房间之际,是身为第一种阶级的一份子(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至少是如此);他走出房间时,就变成第二种阶级的人。至目前为止,他的能量一分为二:企图保住他广告经理的职位,以及想找出他妻子的情人是谁。这两个目标,眼前看来他放弃了第一个。在意识不很清醒的情形下,他察觉到自己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能力正逐渐衰退中;以前他总是相信,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中必存在着理性准则,因此从理性的观点来看,当他无法了解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时,显然这就形成了一个短处。于是这么说吧,他鼓起了余勇,向私人生活中的谜团发动攻势,把最重要的火力放在敌人的身分背景上。而事业就像置于侧腹似的,完全不设防。
安德森在行为上所改变的征状是回办公室后先打电话给依莲·佛莱契利,而非去见威威。她外出去看服装秀。他拨电话到约瑟夫街找佛莱契利,结果没人在家。他去找威威,但他人还在开董事会议。告诉他此事的珍·莱特莉,也回复了他所要求的调查信件掉包的结果。看来是一个热心过头的收发处的小伙子,从珍·莱特莉的桌上拿走了信。当时在收发处那儿,正在收拾广告图稿的时候,他失手让信掉到地上,捡起来之后,把信放错了信封。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对安德森而言,此事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他连那个小伙子的名字都没问。珍说到她希望童装世界没有太生气时,他笑了笑,但是没有搭腔。
对某些人来说,知道最坏的情况会发生,反而会让人松了一口气;至少有一刻,他会因为相信自己可能决断正确而感到沾沾自喜。这会儿,虚假的宁静庇护着安德森。他感觉自己像是判处死刑后上诉失败、而内政部长也拒绝干涉的囚犯一样。明白了无可避免的命运——不就也知道了何谓宁静?温顺而受苦的安德森,正认命地等待着可能的结果,表现得就像大战期间发生空袭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安德森在行为上所改变的征状是回办公室后先打电话给依莲·佛莱契利,而非去见威威。她外出去看服装秀。他拨电话到约瑟夫街找佛莱契利,结果没人在家。他去找威威,但他人还在开董事会议。告诉他此事的珍·莱特莉,也回复了他所要求的调查信件掉包的结果。看来是一个热心过头的收发处的小伙子,从珍·莱特莉的桌上拿走了信。当时在收发处那儿,正在收拾广告图稿的时候,他失手让信掉到地上,捡起来之后,把信放错了信封。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对安德森而言,此事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他连那个小伙子的名字都没问。珍说到她希望童装世界没有太生气时,他笑了笑,但是没有搭腔。
对某些人来说,知道最坏的情况会发生,反而会让人松了一口气;至少有一刻,他会因为相信自己可能决断正确而感到沾沾自喜。这会儿,虚假的宁静庇护着安德森。他感觉自己像是判处死刑后上诉失败、而内政部长也拒绝干涉的囚犯一样。明白了无可避免的命运——不就也知道了何谓宁静?温顺而受苦的安德森,正认命地等待着可能的结果,表现得就像大战期间发生空袭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相关小说
- 你却爱着一个傻逼
- 我深深地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傻逼他不爱你,你比傻逼还傻逼,爱着爱着傻逼的你,我比你更傻逼,简单来说,本文讲述一个,谁比谁更傻逼的故事。 搜索关键字:主角:简隋英,李玉 ┃ 配角:简隋林 简隋英简大少爷好男色的事情简家上下无人不知,连同父...
- 535964字12-26
- 总裁的小妻子
- 那夜,他意识不清地把她当成心爱的女人压在身下辗转承欢......一夜迷情,他在她身体里种下一颗种子......孩子出生,为了留在孩子身边,她卑微的跪在他的面前......一纸不平等条约,她成功的留在了儿子身边,却是以保姆的身份……
- 2658624字06-09
- 霸宠军婚
- 潇湘VIP2013.04.22完结 他是霸道狂野年轻有为的少将, 她是温文尔雅的高智商新闻女王。 在第一次收到天降的未婚夫以后,她的生活注定不平凡。 看一个娇小的小家碧玉怎么变成一个成熟妩媚的女王范, 看一个霸道强势的年轻少将,怎么磨练成一个“小家碧玉”的妻奴...
- 374834字07-06
- 总裁的私有宝贝
- 他是豪门大亨,穆氏集团的总裁!为了救病危的母亲,她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卖给他。原以为,她只是他的工具,他却对她爱护有加;以为他温柔有情,他却害死她最爱的母亲!曾经,他冷酷地说:“按时吃药,因为你没资格生下我的孩子!”她也从来不想生他的孩子!但当她终于从...
- 2462089字04-18
- 豪门劫:冷情总裁的替嫁新娘
- 一场车祸从天而降,她带着姐姐的嘱托,带着姐姐的容貌嫁给她的姐夫,却无端变成害死姐姐的凶手…… 新婚之夜,新郎抛下意乱情....
- 1192345字09-04
- 青囊尸衣4:蛊人
- 古偈曰: 起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 黎明时分,东方现出鱼肚白,清风拂过西峰之巅,仍嗅得到那浓烈的血腥味儿。 草丛微微晃动,一头黑色的小猪崽悄悄探出了脑袋,惊恐的眼神儿四下里警惕的张望着,然后才小心翼翼的走了...
- 532330字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