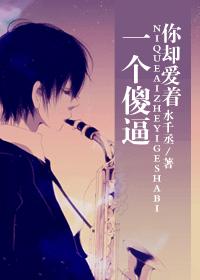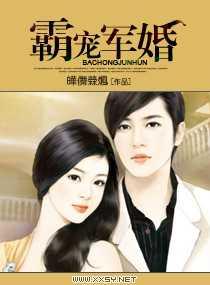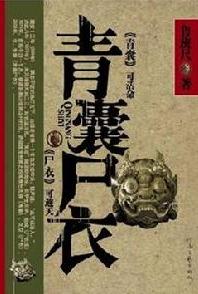第 5 部分(5 / 6)
,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长镀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们的人数尽管并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却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个阻碍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弹在首席检察官米切尔·帕尔默的家门口爆炸,美国政府随即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逮捕了数千名疑似从事激进活动的人。和“9·11”事件后一度笼罩美国的谈虎色变的情绪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红色恐慌”也导致普通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怀疑和恐吓。普通自由派认为,可以使资本主义更为公正,而不至于将其废除。无论如何,当时这派的人数很少。
当时,这只是美国人的视觉盲点。早在1881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他说,政府“也应在国民中为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无产阶层里培育这一理念,即国家不只是个不得已而建的机构,还是个福利机构。必须通过明显而直接的利益来引导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不是一个单为保护社会上层而构建的机构,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服务的机构”。以俾斯麦的德国为先驱,欧洲人早就开始实施类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国政界当时对此还毫无准备、毫无概念。具体而言,英国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养老保险体系,1911年又建立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法国初步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福利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德法三国社会计划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便高于美国,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改变。
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一统天下,其优势地位甚为明显,这成为不利于民主党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年的失败与他的顽固关系甚大,但民主党内的民粹分子对他感到灰心失望还有另一个重大理由:史密斯获提名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对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表忠心。他选择约翰·拉斯科布做竞选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党人、工业家,与自由派唯一明显的共同立场就是都反对禁酒令。史密斯还任命另外4位百万富翁出任竞选班子的领导。事实上,史密斯在选战中将胡佛描绘成一个准备向商界强加政府管制的危险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质上史密斯是作为一个“波旁民主党人”竞选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样,他有可堪匹敌的财力:民主党人花费了530万美元,共和党是630万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纲毫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当时,这只是美国人的视觉盲点。早在1881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他说,政府“也应在国民中为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无产阶层里培育这一理念,即国家不只是个不得已而建的机构,还是个福利机构。必须通过明显而直接的利益来引导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不是一个单为保护社会上层而构建的机构,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服务的机构”。以俾斯麦的德国为先驱,欧洲人早就开始实施类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国政界当时对此还毫无准备、毫无概念。具体而言,英国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养老保险体系,1911年又建立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法国初步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福利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德法三国社会计划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便高于美国,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改变。
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一统天下,其优势地位甚为明显,这成为不利于民主党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年的失败与他的顽固关系甚大,但民主党内的民粹分子对他感到灰心失望还有另一个重大理由:史密斯获提名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对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表忠心。他选择约翰·拉斯科布做竞选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党人、工业家,与自由派唯一明显的共同立场就是都反对禁酒令。史密斯还任命另外4位百万富翁出任竞选班子的领导。事实上,史密斯在选战中将胡佛描绘成一个准备向商界强加政府管制的危险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质上史密斯是作为一个“波旁民主党人”竞选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样,他有可堪匹敌的财力:民主党人花费了530万美元,共和党是630万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纲毫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相关小说
- 你却爱着一个傻逼
- 我深深地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傻逼他不爱你,你比傻逼还傻逼,爱着爱着傻逼的你,我比你更傻逼,简单来说,本文讲述一个,谁比谁更傻逼的故事。 搜索关键字:主角:简隋英,李玉 ┃ 配角:简隋林 简隋英简大少爷好男色的事情简家上下无人不知,连同父...
- 535964字12-26
- 总裁的小妻子
- 那夜,他意识不清地把她当成心爱的女人压在身下辗转承欢......一夜迷情,他在她身体里种下一颗种子......孩子出生,为了留在孩子身边,她卑微的跪在他的面前......一纸不平等条约,她成功的留在了儿子身边,却是以保姆的身份……
- 2658624字06-09
- 总裁的私有宝贝
- 他是豪门大亨,穆氏集团的总裁!为了救病危的母亲,她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卖给他。原以为,她只是他的工具,他却对她爱护有加;以为他温柔有情,他却害死她最爱的母亲!曾经,他冷酷地说:“按时吃药,因为你没资格生下我的孩子!”她也从来不想生他的孩子!但当她终于从...
- 2462089字04-18
- 霸宠军婚
- 潇湘VIP2013.04.22完结 他是霸道狂野年轻有为的少将, 她是温文尔雅的高智商新闻女王。 在第一次收到天降的未婚夫以后,她的生活注定不平凡。 看一个娇小的小家碧玉怎么变成一个成熟妩媚的女王范, 看一个霸道强势的年轻少将,怎么磨练成一个“小家碧玉”的妻奴...
- 374834字07-06
- 豪门劫:冷情总裁的替嫁新娘
- 一场车祸从天而降,她带着姐姐的嘱托,带着姐姐的容貌嫁给她的姐夫,却无端变成害死姐姐的凶手…… 新婚之夜,新郎抛下意乱情....
- 1192345字09-04
- 青囊尸衣4:蛊人
- 古偈曰: 起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 黎明时分,东方现出鱼肚白,清风拂过西峰之巅,仍嗅得到那浓烈的血腥味儿。 草丛微微晃动,一头黑色的小猪崽悄悄探出了脑袋,惊恐的眼神儿四下里警惕的张望着,然后才小心翼翼的走了...
- 532330字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