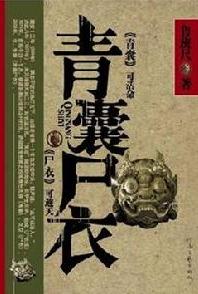第04章(9 / 11)
我做了一些我永远无法收回的事情。对希尔柯·恩格斯坦,我的良心几乎没有受到什么谴责,但对璧德,我差不多真是太不象话了。
另外,我的心里恐惧极了。眼下我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心情;如果有哪个人过来,只要对我稍加怀疑,我的行为立即就会败露了。
星期一早上,我的身体也未见好转;我给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向他们报告说我病了。肠胃引起的流感,我告诉他们。同事祝我早日恢复健康,让我不必起得很早,再赶回公司上班什么的,他们知道我以前那种对工作的责任感,不得不如此提醒我。
要不要顺便往璧德家打个电话,问问她的情况?首先,这是向人表明,我是坚定地认为她是在家里,第二,是想了解一下,是否人家已经找到了她,是否已经开始了有关调查。可是我无法打电话,无法说话,无法哭泣,只有牙齿在不停地打战,人在不停地呕吐。
我的制服穿在身上始终很合体。包括我在家里以外露面时穿着的所有衣服,也都非常讲究和整洁。可当我躺在自己那张孤零零的床上时,我就不必考虑什么了。我的长睡衣,我得承认,很旧很破,但穿着非常舒服,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把它们塞进以后准备送给穷人的红十字会包里。我上次去疗养时,给自己买了两件新睡衣,后来就一直搁在衣橱里,正等待机会穿呢。也许我是该先去趟医院,然后再拿出来穿上。
还是在那个星期一,是下午晚些时候,我就病恹恹地穿着我最旧的缀满小花朵的衬衣(这件衬衣上有因熨烫而烫焦的棕色斑点)耷拉着靠在沙发上,翻阅着一本电视杂志。我老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神,脑子里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正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别开门!接下来的一个念头就是:我现在如此丑陋不堪,是无法出现在人家面前的!但我突然想到,我已经正式请过病假了;很有可能是我的上司将我桌上的急件交给了我的一位同事,然后她过来有什么问题要问。可是她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难道会是上司本人来了吗?绝不可能;毕竟我从不缺席,在我病假的第一天,他既不必来检查我是不是真的病了,也不必给我送花。那么说就是警察来了。
我赶紧穿上一件不怎么样的浴衣,额头上一片冷汗,喉咙里发出恶心的气味,拖着鞋子走到门口。我揿了下电纽,并把房门打开。站在我面前的是维托德,下面的大楼门并没有锁上。
“我的天哪,蒂哈,你的脸色真难看!”他顿时叫了起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另外,我的心里恐惧极了。眼下我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心情;如果有哪个人过来,只要对我稍加怀疑,我的行为立即就会败露了。
星期一早上,我的身体也未见好转;我给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向他们报告说我病了。肠胃引起的流感,我告诉他们。同事祝我早日恢复健康,让我不必起得很早,再赶回公司上班什么的,他们知道我以前那种对工作的责任感,不得不如此提醒我。
要不要顺便往璧德家打个电话,问问她的情况?首先,这是向人表明,我是坚定地认为她是在家里,第二,是想了解一下,是否人家已经找到了她,是否已经开始了有关调查。可是我无法打电话,无法说话,无法哭泣,只有牙齿在不停地打战,人在不停地呕吐。
我的制服穿在身上始终很合体。包括我在家里以外露面时穿着的所有衣服,也都非常讲究和整洁。可当我躺在自己那张孤零零的床上时,我就不必考虑什么了。我的长睡衣,我得承认,很旧很破,但穿着非常舒服,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把它们塞进以后准备送给穷人的红十字会包里。我上次去疗养时,给自己买了两件新睡衣,后来就一直搁在衣橱里,正等待机会穿呢。也许我是该先去趟医院,然后再拿出来穿上。
还是在那个星期一,是下午晚些时候,我就病恹恹地穿着我最旧的缀满小花朵的衬衣(这件衬衣上有因熨烫而烫焦的棕色斑点)耷拉着靠在沙发上,翻阅着一本电视杂志。我老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神,脑子里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正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别开门!接下来的一个念头就是:我现在如此丑陋不堪,是无法出现在人家面前的!但我突然想到,我已经正式请过病假了;很有可能是我的上司将我桌上的急件交给了我的一位同事,然后她过来有什么问题要问。可是她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难道会是上司本人来了吗?绝不可能;毕竟我从不缺席,在我病假的第一天,他既不必来检查我是不是真的病了,也不必给我送花。那么说就是警察来了。
我赶紧穿上一件不怎么样的浴衣,额头上一片冷汗,喉咙里发出恶心的气味,拖着鞋子走到门口。我揿了下电纽,并把房门打开。站在我面前的是维托德,下面的大楼门并没有锁上。
“我的天哪,蒂哈,你的脸色真难看!”他顿时叫了起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相关小说
- 你却爱着一个傻逼
- 我深深地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傻逼他不爱你,你比傻逼还傻逼,爱着爱着傻逼的你,我比你更傻逼,简单来说,本文讲述一个,谁比谁更傻逼的故事。 搜索关键字:主角:简隋英,李玉 ┃ 配角:简隋林 简隋英简大少爷好男色的事情简家上下无人不知,连同父...
- 535964字12-26
- 总裁的小妻子
- 那夜,他意识不清地把她当成心爱的女人压在身下辗转承欢......一夜迷情,他在她身体里种下一颗种子......孩子出生,为了留在孩子身边,她卑微的跪在他的面前......一纸不平等条约,她成功的留在了儿子身边,却是以保姆的身份……
- 2658624字06-09
- 总裁的私有宝贝
- 他是豪门大亨,穆氏集团的总裁!为了救病危的母亲,她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卖给他。原以为,她只是他的工具,他却对她爱护有加;以为他温柔有情,他却害死她最爱的母亲!曾经,他冷酷地说:“按时吃药,因为你没资格生下我的孩子!”她也从来不想生他的孩子!但当她终于从...
- 2462089字04-18
- 霸宠军婚
- 潇湘VIP2013.04.22完结 他是霸道狂野年轻有为的少将, 她是温文尔雅的高智商新闻女王。 在第一次收到天降的未婚夫以后,她的生活注定不平凡。 看一个娇小的小家碧玉怎么变成一个成熟妩媚的女王范, 看一个霸道强势的年轻少将,怎么磨练成一个“小家碧玉”的妻奴...
- 374834字07-06
- 豪门劫:冷情总裁的替嫁新娘
- 一场车祸从天而降,她带着姐姐的嘱托,带着姐姐的容貌嫁给她的姐夫,却无端变成害死姐姐的凶手…… 新婚之夜,新郎抛下意乱情....
- 1192345字09-04
- 青囊尸衣4:蛊人
- 古偈曰: 起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 黎明时分,东方现出鱼肚白,清风拂过西峰之巅,仍嗅得到那浓烈的血腥味儿。 草丛微微晃动,一头黑色的小猪崽悄悄探出了脑袋,惊恐的眼神儿四下里警惕的张望着,然后才小心翼翼的走了...
- 532330字09-18